【柳氏医派】柳少逸:读《史记》 论扁鹊在中国医学史中的地位——“扁鹊言医,为方者宗。”

读《史记》 论扁鹊在中国医学史中的地位(1)
——“扁鹊言医,为方者宗。”
【按】扁鹊,原名秦越人,为先秦时期最著名的医学家。其受业于长桑君,又授徒子阳、子豹等弟子十余人。越人医术精湛,内外妇儿诸科均有所成,行医于战国时中原诸国,且能“随俗为变”。在赵为“带下医”;至周“为耳目痹医”;入秦“为小儿医”,从而“扁鹊名闻天下”。故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序,弗能易也”;“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从而在史学上确立了秦越人为医学鼻祖的地位。(柳少逸)
金·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叙》中尝云:“夫医道者,以济世为良,以愈疾为善。盖济世者,凭乎术;愈疾者,仗乎法。”秦越人以高超的济世之术,神奇的愈疾之法,构建了中医学术体系之雏形,创建了扁鹊医学流派,成为亘古至西汉集中国医学之大成者第一人,从而确立其为一代宗师的地位,所以成为太史公在《史记》中立传的医学界第一人。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说明自黄帝轩辕始,历代贤哲,根据自然法则及人们的需要有众多的发明和创造。对此荀子有云:“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的论述。表述了黄帝时代的制作与发明及其传人,但未论及是谁发明医学。
据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方伎略》中“方伎者,皆生生所具。”“方伎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故“医经者”,乃讲述人之生理、病理及诊疗技术,为理也,法也,广义之方也。“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热宜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於外,是所独失也。”故“经方者”,乃讲述药物的性味归经、配伍应用,及用药失误对人体的危害。乃专论方药属狭义方之含义,但仍寓方药于法中。诚如明·李士材在《伤寒括要》中所云:“方者,定而不可易者也;法者,活而不可拘者也。非法无以善其方,非方无以疗其症。”
对“方”的含义,历代文献皆有所述。如《诗·大雅》云:“万邦之方,下民之王。”毛传注云:“方,则也。”《易·系辞》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孔颖达疏云:“方,道也。”方谓法术性行,故广而言之,方者,法也。准则、义理、道理之谓也。《庄子·逍遥游》云:“客闻之,清灵其方百金。”《隋书·许智藏》云:“智藏为方奏之,用无不效。”《潜夫论·散论》云:“凡治病者,必先知脉之虚实,气之所结。然后为之方。”故约而言之,方者,药方、单方也。
清·张山雷《论方案》云:“方者,法也,必有法事可云方。”沈金螯《伤寒论纲目》云:“夫方因法立,法就方施。”从而形象地论及方(狭义方)与法(广义方)的辨证关系,即方中有法,法中有方。它如同一方药,根据病情需要,可有不同的剂型。对此清·宝辉在《医医小草·精义汇通》中有如下的精辟论述:“方有膏、丹、丸、散、煎、饮、汤、渍之名,各有取义。膏取其润,丹取其灵,丸取其缓,散取其急,煎取其下达,饮取其中和,汤取其味,以涤荡邪气,渍取其气,以留连病所。”由此可见,药物的运用,尚有众多的不同的方法。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可知,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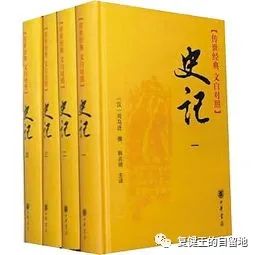
晋·黄甫谧《甲乙经·序》记云:“中古名医有俞跗、医缓、扁鹊,秦有医和,汉有仓公,其论皆经理治本,非徒诊病而已。”但俞跗、医缓、医和在《史记》、《汉书》中均未见传,除越人外均无著述。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可知,公乘阳庆传仓公之禁方中。有“扁鹊之脉书”;《汉书·艺文志·方伎略》“医经七家”有《扁鹊内经》九卷《扁鹊外经》十二卷;“经方十一家”中有《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就“诊籍”而言,只有在被誉为“信史”的《史记》中有多处记载。故曹东义在《神医扁鹊之迷》中认为:“从古籍由简而繁的发展趋势看,《白氏内外经》应晚于《黄帝内外经》,当然更晚于《扁鹊内外经》……此与汉儒传经有相似之处,儒经源于六艺,而医经发端于扁鹊。”由上所述,《扁鹊内外经》的内容已佚。现今已无从考之。但多存于《内经》之中。《扁鹊内外经》的内容,尝可从《难经》谈起。李昉《文苑英华》杂序类,引唐·王勃《黄帝八十一难经》序称“秦越人始定章句”,此即秦越人著《难经》说。宋·苏轼《楞伽经跋》云:“医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后世达者,神而明之。”清·叶霖《难经正义》序云:“世传之《难经》者,杨玄操序言渤海秦越人所作,殆难穷考,而仲景《伤寒论》自序,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云云,其为汉以前书无疑,当是史迁《仓公传》所谓扁鹊之脉书也。”欧阳玄《难经彙考》云:“切脉于手之寸口,其法自秦越人始,盖为医之祖也。《难经》先秦古文,汉以来答客难等做,皆出于后。”杨玄操《释幻云史记附标》云:“黄帝八十一难者,斯乃渤海秦越人所作也”。就《难经》的内容而论,滑寿云:“一难至二十一难皆言脉,二十二难至二十九难论经络、流注、始终长短,度数奇经之行,及病之吉凶也。其间有云:‘脉者非谓尺寸之脉,乃经隧之脉也。三十难至四十三难言荣卫三焦脏腑肠胃之详。四十四、五难言七冲门乃人身资生之用,八会为热病在内之气穴也。四十六、七难言老幼寤寐,以明气血之盛衰,言人面耐寒以见阴阳之走会。四十八难至六十一难,言诊病能脏腑积聚泄利伤寒杂病之别,而继之望闻问切,医之能事毕矣。六十二至八十一难言脏腑荣俞用针补泻之法。”又云:“唐诸王侍读张守节作《史记正义》,於《扁鹊仓公传》,则全引《难经》文以释其义。后全载四十二难,与第一难、三十七难全文。由此则知,古传以为秦越人所作者,不诬也。”从《难经》中可知,《难经》的诊法多为“色脉之道”,其治疗方法多为“脏腑荣俞用针补泻之法”,由此可窥见扁鹊学派的学术思想和医学知识结构。尤其《难经》中有云:“脉者非谓尺寸之脉,乃经髓之脉也。”,乃通过经络系统以诊查疾病也。脉乃“经脉”、“脉学”、“诊法”之谓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扁鹊“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癥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之言,讲的是以扁鹊学派的“诊法”查病,可“尽见五脏癥结”。特以狭义之诊脉之切诊冠名,故太史公有“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之论。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讲述了扁鹊秦越人受业
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可知“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于是召扁鹊。扁鹊入,“视病”。扁鹊以其独特的脉色诊法,认为赵简子“血脉治也”,“不出三日必閒。”果然,“居二日半,简子寤。”它如过虢诊太子尸厥案时之自述:“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为不诚,试入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于阴,当尚温也。”此即《 扁鹊传》中所述:其诊法得长桑君秘传,“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癥结”。在治疗虢太子病时,“扁鹊乃使弟子子阳厲鍼砭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閒,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剂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更适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通过上述文献资料可知,扁鹊不但具有很高的诊断技术,同时尚掌握了药物疗法与非药物疗法及内服法与外治法等众多的卓有成效的临床治疗技术。清·赵学敏《串雅内编·诸论》中有云:“周游四方,俗呼走方医。其术肇于扁鹊,华佗继之。故其传与国医少异。外治以针刺、蒸灸胜,治内以顶、串、禁、截胜。”禁法为药物与祝由相结合;截法为单方重剂;顶法为催吐法;串法为泻下法。战国时期,官学没落,为了生计,医官、医师流入民间,加入走方医的行列,故形成了长桑君、扁鹊这样的走方名医。扁鹊及后世华佗属“走方医”,其典案多系急症,故多用针灸、药熨、按摩等外治法,以救其急,待病缓,再以汤剂,图其愈病。所以不能“以针灸立法为医经学派”,“以方药立论为经方学派”,只能分“药物疗法”和“非药物疗法”两大法门。先秦时期,药物方法多是单味药应用,配伍应用尚处萌芽状态,故有《本草经》形成。该书标志经方起源,在“汤液经法”、“经方十一家”形成以后,标志了经方理论的形成,至《伤寒论》传世,经方理论体系则得已完善。
《礼记》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唐·孔颖达《礼记正义》云:“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 “三世之书”提示了自古就形成了中医学的三大知识结构,一是以伏羲氏制九针的传说,到总结成《黄帝针灸》;二是从黄帝、岐伯讨论脏腑经脉的传说,到总结成《素女脉诀》;三是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到总结成《神农本草经》,于是形成了后世所称谓的“三世医学”。此乃先秦医家必备的医学知识结构。它的内容为《黄帝针灸》(即今之《灵枢》)、《神农本草经》、《素女脉诀》(发展形成《素问》与《难经》),于是,由于书名的变更,“三世之书”即今天我们所说的三大经典著作:《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当是今天良医的知识结构,亦为“方者宗”也。从《史记》中所记载的扁鹊所承传的诊疗技术,《汉书》中所记载的扁鹊的医学著作,及传《难经》为扁鹊所著来看,广义之“方”,概含了医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及临床诊疗技术。故尔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并非过誉。
【注】本文节选自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柳少逸著《柳少逸医论医话选》2015年4月第一版“读史记,论扁鹊”。